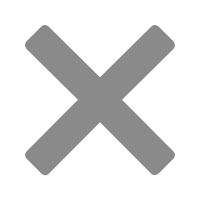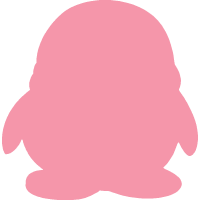-
老公将女儿的骨髓给白月光儿子
本书由梦阅原创小说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1
“很抱歉,医院库中的骨髓不足,我们已经尽力了,节哀。”
我不可思议地报告质问着面前的主治医院:“明明昨天是你亲口告诉我有合适的骨髓,怎么会突然就没有了呢?”
张医生无奈叹气:“这件事情,或许陆医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解释。”
看着人远去的身影,我不敢相信这一切,他口中的陆医生,正是我的老公,孩子的父亲。
拿着手机的手微颤,拨打二十多个电话都无人接听。
看着我女儿缓缓地被推出来脸上盖着白布,我心痛到极点,还未触碰到她,眼前一黑昏了过去。
再次醒来的时候看着病房里的一切,我坐起身,床头柜上多了一个白瓷瓶。
我妈妈激动地过来握着我的手,眼睛红肿:“醒了就好,醒了就好,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?”
嗓子里被翻涌的情绪堵住,我轻轻地触碰那静静放着的白瓷瓶。
妈妈拉过我的手,轻轻地将我揽在怀中:“生病太苦了,星鸾先去下一世看看,别伤心啊,医生说你的病情恶化,如果你……可让妈妈该怎么办啊。”
看着那白瓷瓶,很难想象一个打针都怕疼的小女孩,在手术台上得多么煎熬。
我小心翼翼地把公主裙烧过去,那本是我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,只不过再也没有机会穿了。
裙摆上的小蝴蝶结掉落在我身上,就仿佛那个小丫头还趴在我身上一样。
从手术到现在已经有三天时间,可是我的老公陆昀,一次都没有给我回过电话。
我当然知道他的消息,整个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收到他儿子手术成功的喜糖。
我抱着白瓷瓶坐在沙发上等男人回家,就算是离开,我也想了结这一切。
陆昀一直到下半夜才回来,满身的香水味让人觉得恶心,懒散地躺在沙发上:“去给我做顿饭,我还没吃饭。”
我淡然地看向一旁的男人:“我们离婚吧。”
陆昀不可思议地坐起身,嗤笑道:“就凭你一个家庭主妇,你要是敢和我离婚,一分钱捞不到就算了,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星鸾一面。”
我轻轻地安抚手中的白瓷瓶,坚定起身:“明天早上民政局见。”
没走几步,男人再次开口:“我劝你脑子清醒一些,星鸾的骨髓我一定会有办法,你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跟我斗气。”
男人的话语中充满了不耐烦,仿佛我才是那个骂街的泼妇。
他们一家三口和乐融融庆祝的时候,是踩在我女儿的尸骨之上。
眼看我就要推门离开,男人一把冲过来拉过我的手,白瓷瓶掉落在地上。
“我跟你说了多少遍,医院有更重要的人需要那份骨髓,星鸾是我的亲生女儿我会看着她忍受病痛吗?”